好友浏览过怎么又看不见了微信 好友浏览过为什么不显示
好友浏览过怎么又看不见了微信 好友浏览过为什么不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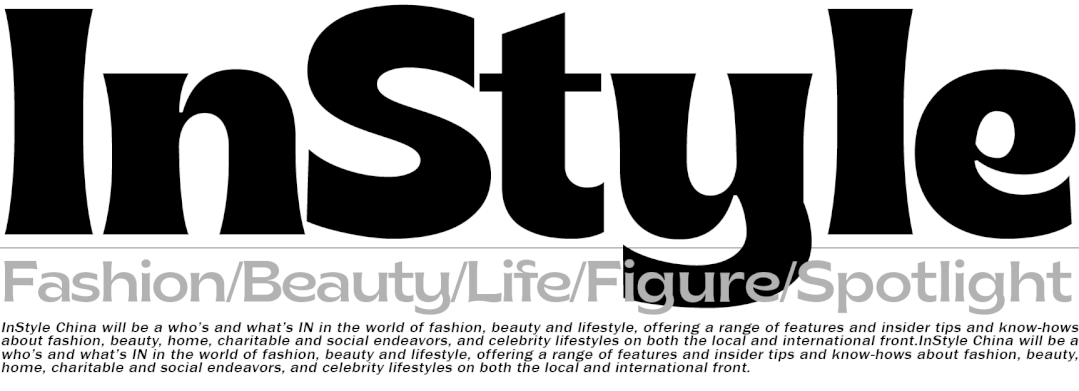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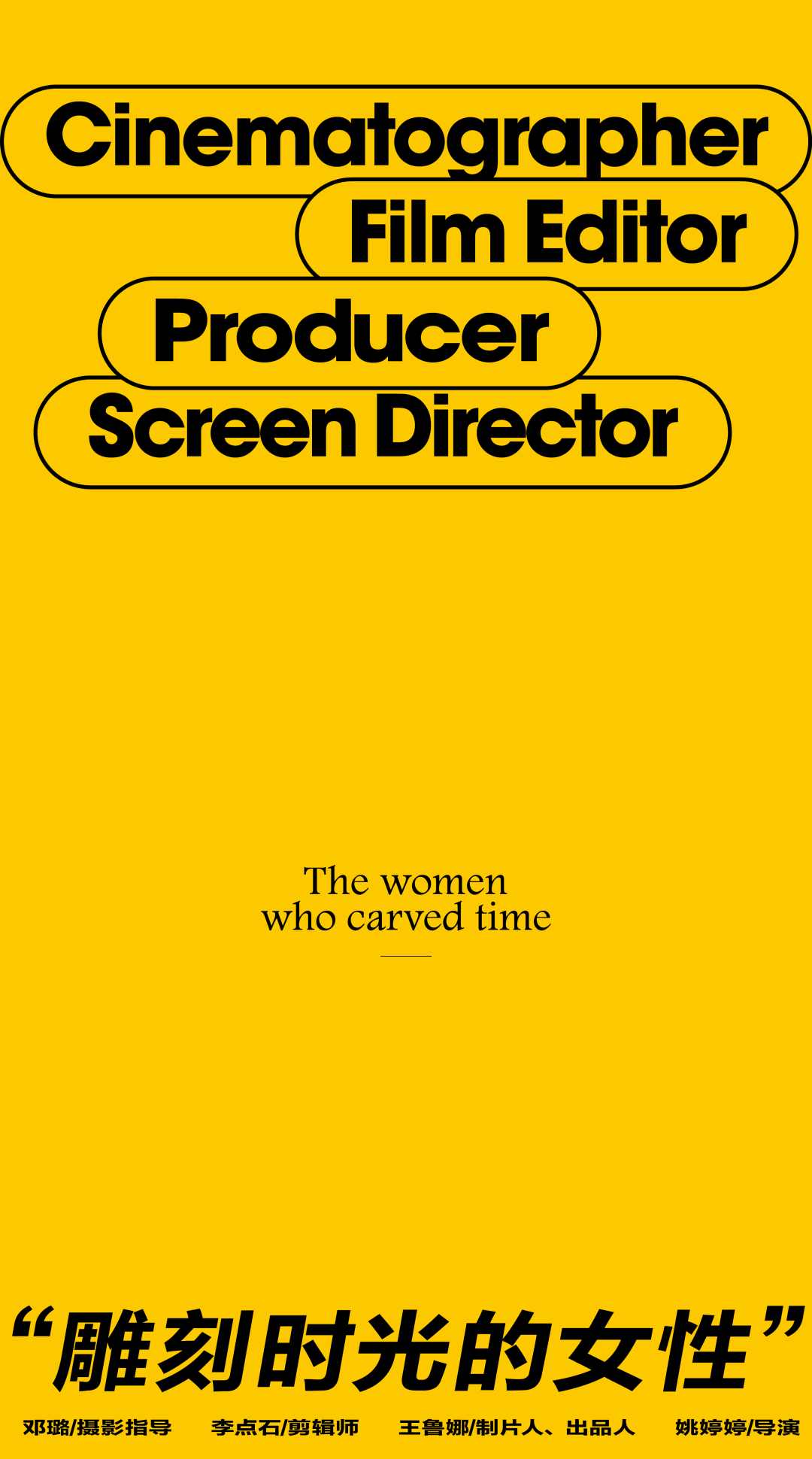

上海国际电影节将魔都变成了一个由光影编织成的枢纽,开埠等待人们坐进电影院,连接不同年代和中西的故事。如同咖啡,电影对上海市民来说更像童年时候就拥有社会身份的硬需。一个人或携伴,无论于私人还是公共的体验里都需要电影这个场景来承载现实生活中的爱恨情仇。
早年住在常德公寓的张爱玲爱吃蝴蝶酥,爱去大光明电影院。那么多年后,《爱情神话》上映,上海的老阿姨们在电影院里依旧爱吃蝴蝶酥,一面点头说着“老灵咯”。乱世和盛世里,电影用某种历史书写的方式,通过味道、记忆,把这些“偷欢”时刻用影像留了下来。
电影有内外部时间,自诞生以来就由技术来做视听语言,把内部的心理时间伸长或压缩,容得下客观时间的流逝,让人走进暗室体验。电影本质又是大众商品,只不过能印上个人记忆的存证。往往男人觉得天色尚早,女人却叹春光已老。在这些变幻的主客中,这一期InStyle选取了四位女性电影从业者,让她们讲述,在时光里与电影如何雕刻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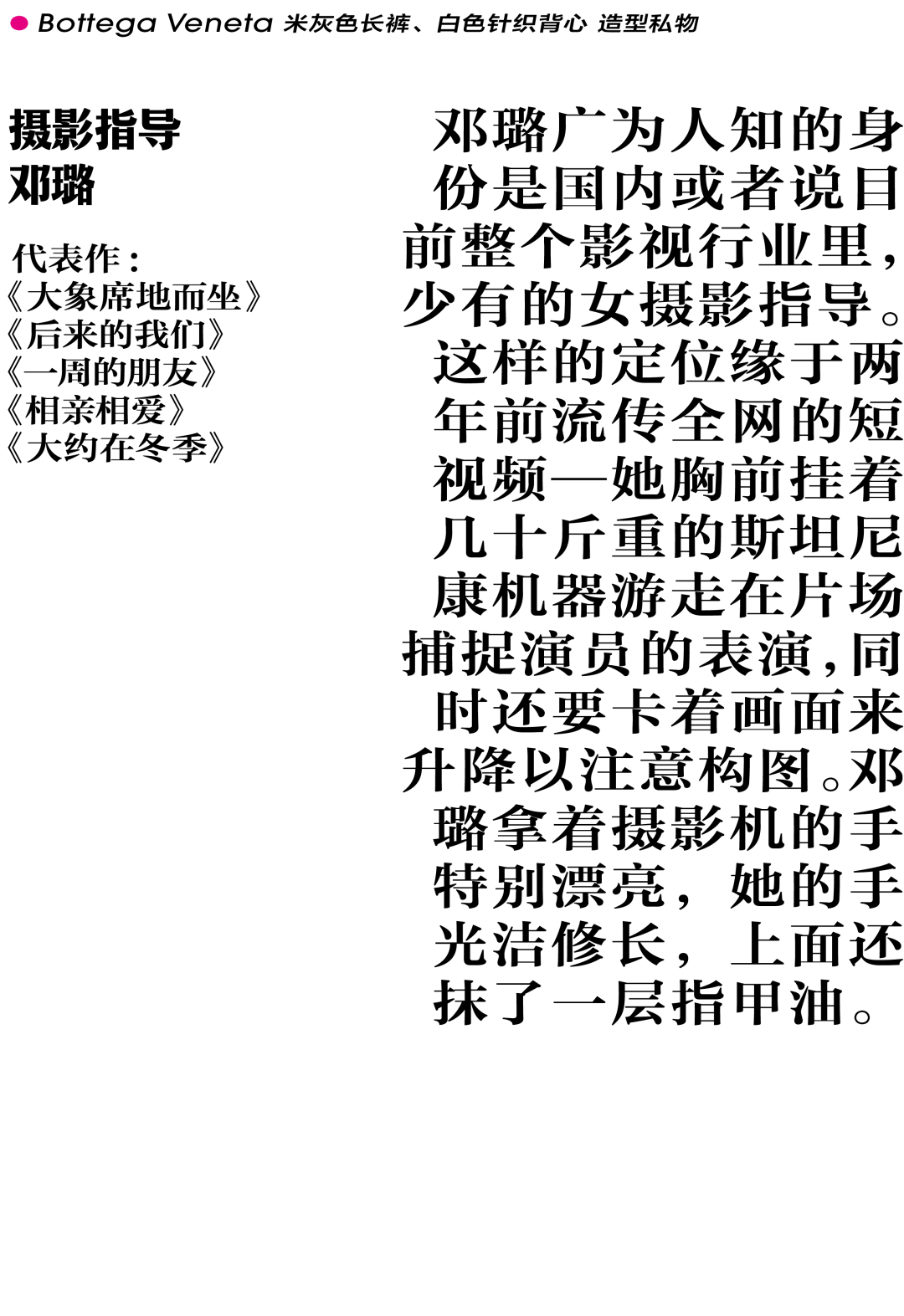
邓璐最不喜欢别人觉得她只是因为力气大到能和男人拼体力才做的摄影师。
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误解。
电影摄影师本来就是一个电影技术工种,体力只是幕后工作者的普通标准。但她也不愿意去解释自己,最后索性连为什么健身,还有自己身上肌肉骨骼受过的伤痛都一并不讲了。在她看来,职业不太需要解释,只需要展示。
是什么能达到展示的效果呢?斯坦尼康只是电影摄影工具中的冰山一角,还有更多技术、细节、光线、色彩,包括镜头语言在决定影像中的好坏,是业务能力还有平台提供的展示基础。如果条件有限,用手机也能拍出好的作品。邓璐转行从事摄影初期为了争取机会,给自己立的斯坦尼康目标是一万个小时。只是在这一万个小时里面,大家对她注意的点更多的是年轻女摄影师,力气大,能扛斯坦尼康。

MaxMara 藏蓝色衬衫、阔腿长裤
Bottega Veneta 高跟鞋
邓璐的微信和抖音名叫“邓璐也叫璐小仙”,这个名字是因为朋友们觉得她有第六感并且总是很准。她很喜欢二手玫瑰的一首代表作《仙儿》,里面有一句歌词:念天念地念知己,望山望水我望清晨。
业界很多人在没接触邓璐之前,一方面觉得她是女性,这行业女的基本干不下来,因此对她有一种猎奇心理;一方面又觉得她是李屏宾带出来的徒弟,报价特别贵。摄影师李屏宾先生是当代电影摄影指导中殿堂级的人物,拿过七次金马奖,还拿过戛纳和柏林电影节的奖项。邓璐第一次遇到他是因为《相亲相爱》,灯光师向李屏宾推荐了邓璐,当时邓璐又激动又忐忑,很担心李老师会介意自己是女掌镜,另一方面她怕自己无法达到令他满意的效果。
在影视圈,无论是摄影师还是制片、导演、武行等基本上都需要师父带,跟着团队,大家一起接活,像走江湖一样,大哥带着领路才能出得来。邓璐其实是半路出家,学生时代她学的是动画专业,虽然家里姥爷和父亲是摄影师,但摄影这方面手艺活都是传男不传女。她为了走上摄影这条路,坚信勤能补拙与能者多劳。无论是理论知识、熟练技能还是体力都要保持时刻准备着的状态。但没有固定的师父带,更没有什么团队给她容身之处,转行从事摄影后的她就像个流浪的孩子,哪里缺人或是替补请假,哪里才会喊她来补。

在第一次和李屏宾合作的剧组里,邓璐内心知道大家对她拍的东西并没有那么满意。一天的戏拍下来每个人都累得够呛,装完机器收工,邓璐趴在金杯车上看着李屏宾,他也笑着回看了邓璐,邓璐盯了几秒钟后挤出一句话,能不能跟您合个影。李屏宾说,行啊。再接着摄影组的人一起喝了个酒。临走的时候,车上的助理就问她,你没跟宾哥留个联系方式?邓璐说,我没留。他问,为什么?邓璐讲,我觉得我没脸留,我对这次自己拍的不满意。回去再努力练练,假如命运觉得我够资格了,自然就会相见了,一切就交给努力与命运吧。
结果在第二年,又是同样的情形下,邓璐与李屏宾再次合作了。邓璐说,那次是带着训练了一整年的成果,以一雪前耻的态度去的。后来跟随李屏宾老师拍摄至今,她终于不再是一个在行业里飘荡的野孩子,终于名正言顺有了一个师门。邓璐的仙儿其实有一种莫大的笃定,动画训练的学习背景让她知道摄影指导该做的镜头拆解怎么做,故事板要怎么绘,用镜头怎么把一个故事从文本当中翻译出来。决心做摄影后,吃了好些苦头,把器材技术都摸会了,身体、意志一个不缺的情况下,她等着命运光临自己。

摄影师这个工作并不是只有大家所看到的她背着沉重的机器在片场游走,还包括特别多的前期的案头,还有跟导演,服化道,场地制片等各个部门的沟通。这意味着,她必须是剧组里情绪最稳定的人。她在工作的时候,要做观看演员的眼睛,捕捉他们最好的表演。有时候需要隐藏自己的存在,但有时候也要给他们方位感。在各种情况都可能发生的情况下,导演的压力往往是最大的,而承担这些情绪和后果的,首先也是邓璐。
她在严冬的野外,快过年的时候,手冻得麻木红肿,扛着机器的时候还因为行动速度太慢被剧组的人踹过。她因为扛得动那么重的机器,很多人除了觉得她不容易,还潜意识里默认她肩上也能扛得动其他不该她承担的负担。不管是新人导演的不成熟,还是剧组的超时大夜戏,抑或演员的状态不好等等,只要是有意外发生,她都必须去解决,因为镜头永远需要开机记录,她要对拍下来的东西负责。
在拍《一周的朋友》时,有一场戏是林一对赵今麦一见钟情,但没有台词,全部用镜头语言来完成这个表达。邓璐说这样的一见钟情,其实就是她回想自己想成为摄影师的时候,记起那个最初的誓愿,像奶油蛋糕上那个新鲜、甜美的草莓,缓缓地在眼前放大,拉到自己身边,并用一万个小时的时间来品尝回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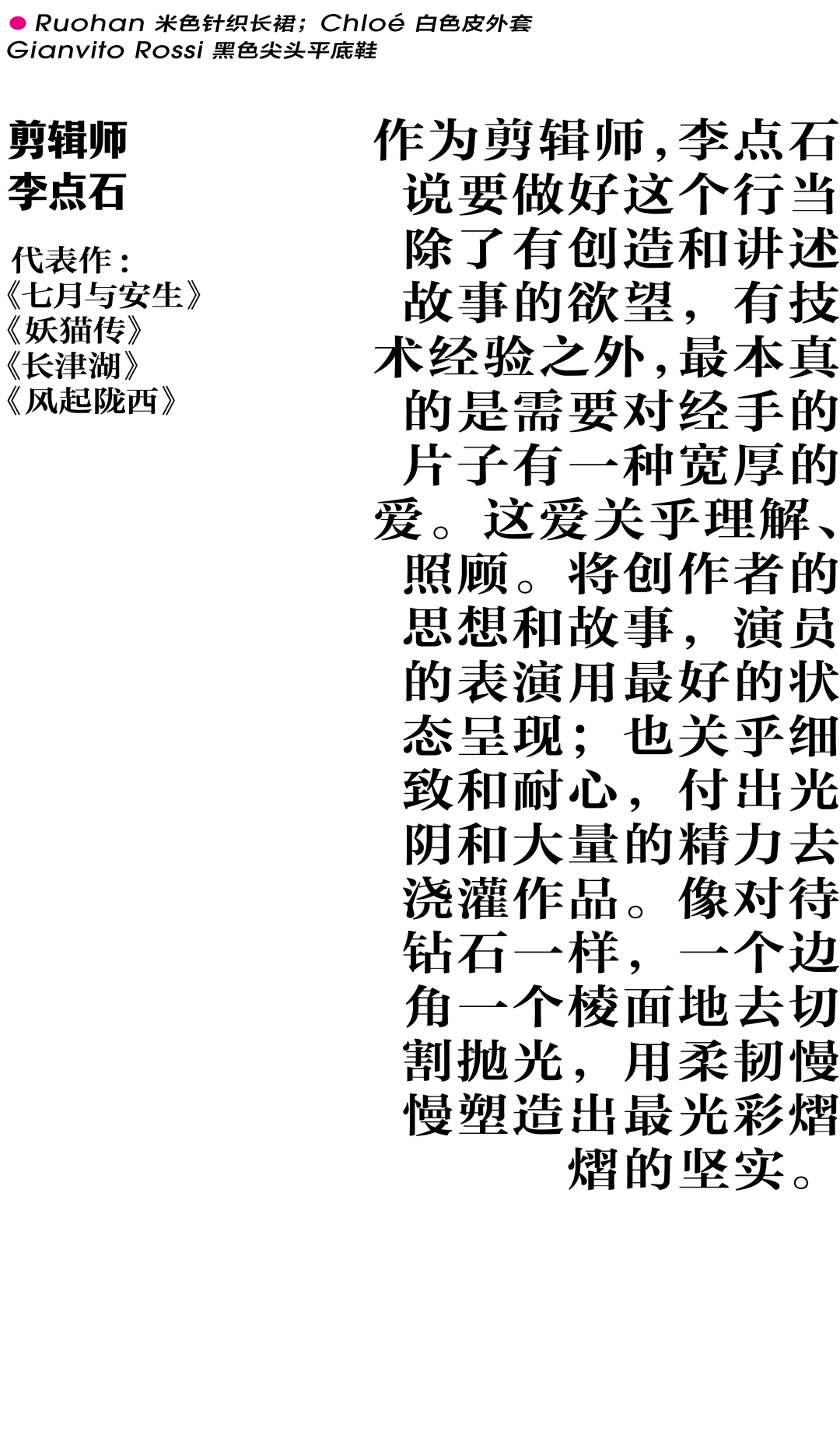
这篇访谈成文当天,恰逢李点石剪辑的电影《少年时代》定档。这部影片原名《尘埃里开花》,2019年拍摄,历经4年时光终于得以上映。
她回想这期间面对的无数次修改与挫折,遗憾和辛苦,这一切都包容在终于落定的尘埃中,开出属于电影的花。电影有个理论叫镜像凝视,意思是银幕就像镜子,在观看初期,观众与银幕中的形象产生自恋式的认同,当电影将虚构的故事搬上银幕,观众发现他在自己所凝视的银幕上并不存在。尽管观众从银幕上缺席,但因为电影的意义正在于观看,观众又作为看与听的主体而在场。连续性剪辑与视线匹配原则,如“正反打”就让观众不断拥有两个人的视点,在观看者与被看者的位置上不断转换。观众认为自己处于“既在看,又没有被看”的偷窥位置。



电影《少年时代》剧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点石就是她所剪辑电影的第一个观众,她不仅要承担这种在场和不在场的凝视,还要把这些零零碎碎的镜像缝合在一起,变成适合其他观众来看的作品。为了更好地表现人物和故事,她需要移情成里面在场的人。
细节到一场戏,可能拍了很多条,她要选择表演最出彩的一条,而这种判断也要和导演最终不谋而合;宏观到需要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价值观,在这样的层面去俯瞰故事和结构。剪辑不仅仅是一刀刀去剪,一条条去连接,更是不断从观看主体到客体的相互转换。用情绪带领着时间,也用结构组织着时间。
李点石说,真正好的剪辑师真的不只是帮导演去接得很顺、剪得很花很漂亮而就这么结束了。这些不过是需要做的基础事儿,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好的剪辑师,应该更往上走,更俯瞰整个全局的东西。要在别人的工作上,接着进行讲述的创作。

Tod’s 半透明针织上衣、棕色皮质半裙
Gianvito Rossi 黑色尖头高跟鞋
李点石的起点非常高,以当年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也是导演系招收的第一届本科剪辑方向的学生。她刚毕业就参与了顾长卫《最爱》的剪辑工作。她说,其实剪辑并不是靠天分的工种,她第一部戏就非常痛苦,因为剪辑是需要实操经验去辅助的。驾驭一部长片的能力需要很长时间的磨练,然后你才能够大概了解那种节奏,心中形成一种感觉。她当时的痛苦是,知道哪里可能有问题,哪里不对,但不知道怎么去最终解决这个问题。仿佛在一个迷宫面前,有无数分岔的路口,还是连贯性的。
她没有那么多的确定性,只能一条条路径去试。她强调,这是一个手艺活。技术和经验到那里了,那么你就会像一个有经验的司机,知道路线的规划。这也是为何从毕业至今,她一直在一部一部戏,不断积累和磨练。经验和阅历让剪辑师逐渐成熟,才能从容地面对每一部作品。



在电影的每个制造链条里面,永远有对抗和对不可抗力的妥协。剪辑师已经是摄制组中较少需要跟人发生密切交集的岗位,但对内也仍需面对导演、制片人,为内容的完整和质量把关,对外还要面对市场、审查机构,去把控影片的商业性和尺度。但李点石始终认为,电影是一个主观的创作。创作者用自己的思维构筑故事和人物,用电影向观众输出表达。剪辑师的任务,不是把电影雕琢成一个依靠数据、试片意见生产的符合最大公约数期待的完美商品,而是应该以此为参考,让创作者的表达更加充分和易于接受。
内行看的不仅仅是门道,电影对于李点石有更多时间上的重量,尤其是看自己的电影。一部90分钟的电影,有时会需要半年到一年的剪辑工作时间。在重新观看完片的时候,其间的点点滴滴,像一个镜子又映射过来了一样,李点石会想起当时自己所处的年龄,心境,是什么促使自己在那个时候做了那些选择,选择了那些素材,接法,音乐节奏,最终生成了这样的结果。在最后上映之前,她已经看了无数遍这些素材了,像困在一个不断循环的河流中,重复体验着自己的人生。电影上映之时,仿佛一场放生,如同《西游记》的最后,唐僧历经各种苦难,看河上漂着自己的一具皮囊。
李点石说,人们在电影院看一个多小时的片子是用自己几百个小时的青春去灌溉的,用自己的真实的时间,用客观的物理时间堆积而成,是每天雷打不动早上起床坐在这儿冲一杯咖啡,然后开始工作直至休息。她说,有一句话特别打动自己。这句话是:吾等采石之人,当心怀建造大教堂之愿景。这也是她在日复一日的枯燥工作中,始终心怀的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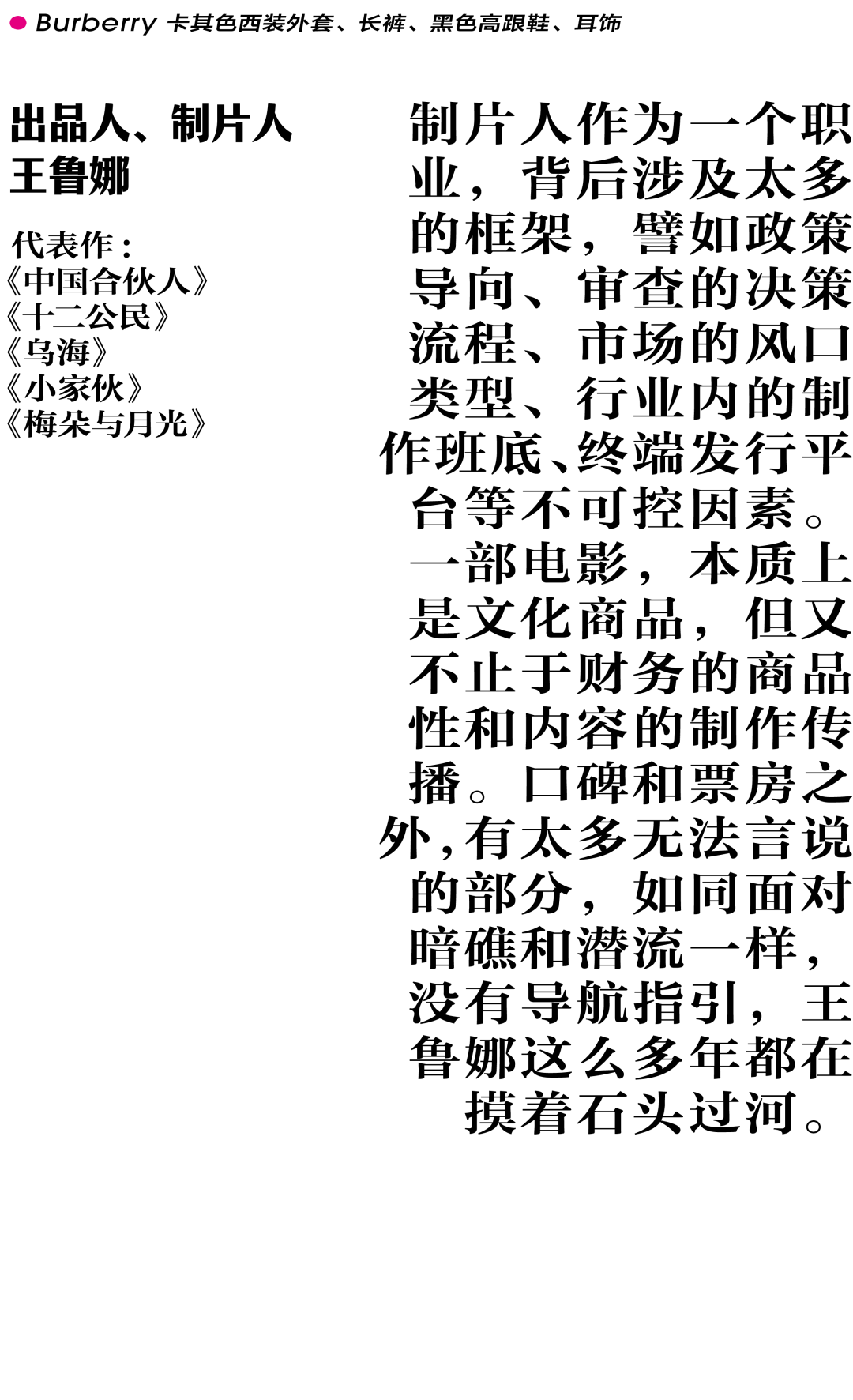
“做制片真的是一直在交学费。”每当别人问,你怎么总结做制片这些年来的感悟,王鲁娜总是先笑着哎呀叹口气,然后说出这句话。她总是很谦逊,说自己不像科班出身的人,很多东西一上来就知道怎么做。在她的职场生涯中,新东方和真格基金给了她最早的起点,老板徐小平和王强都是老师,这赋予了她终身学习的基因。加上山东人骨子里的勤奋和不屈不挠,王鲁娜转到影视当制片人,一晃眼已经十年了,她还是在学。交的学费已经远不止影视行业里投资受到的财务损失,还包括为了实现广义上从内容到意识形态的认知,如何降落到全球化的市场里,而付出的努力。
拍摄采访的前一天,她刚从延安回来。参加中国文联举办的全国中青年文艺领军人物人才高级研究班,班上每个人要自我介绍,其他人拿出书画作品,还有人载歌载舞,她做了一个视频,把十年做电影制片和出品的片子预告片串联了一下,数了数,十年正好十部。

Prada 藏蓝色针织开衫、白色衬衫、
藏蓝色针织半裙、白色半裙、黑色高跟鞋
从《中国合伙人》开始入行,到2020年上映的《乌海》,王鲁娜说,一回顾发现全是男的群像和大男主的戏。倒是这两年一直想跟女导演做一点女性项目。以往在她主控的项目上,她特别怕的就是陷入到那种自我怜爱的境界里。在进入这个行业后,她下意识觉得需要跳出细节视角去看这个世界。制片和出品最终面对的是市场环境,而不光是内容和创作者本身,所以她得保持点距离,试图把熟悉的东西陌生化一点。仿佛到现在这个阶段是个节点了。考虑接下来想做女性题材的东西,是因为她本身没有做过这些类型,另外在之前做一些男性的片子的时候,在回望自己的性别的时候,反而有一些新的感悟和思考。两性是绕不过去的主体,那么有这些宏大的,男性作为表达主角的片子打底之后,再来做女性的题材就会有更多的参照体系。

电影《乌海》剧照
其实“交学费”这件事在背后更本质的是对王鲁娜的改变,使她更能客观地从全局定位自己,一点点地获得自信。在中国的电影市场里,没有人敢说自己有一定的经验方法论。电影项目从生产出来到投放市场,2年已经算快的,5年也是非常正常的周期,但现在的市场是以月为时间单位发生变化的。
王鲁娜说,上个月跟下个月它的这种政策环境、经济环境,以及所有的同行资源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导演是整个链条当中前面的部分,而她身为制片人要完整地跟项目,直到最终跟市场短兵相接。出品加上制片,不光是名称荣耀,更是要承担你自己的投资的所有风险,所以那种扑面而来的残酷性和那种变化性,直接决定了这个工种成熟期会特别晚。
在电影行业还在飞速发展,市场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作为制片人还可以拥有很多情怀,因为项目留有一些空间能任性一点,跟导演一起做尝试。但现在不允许了,王鲁娜觉得这是对导演的一种保护,因为最终大家还是要面对市场。有些导演不用对资本负责,可能还在享受最终上映之后的奖项或者一些掌声,亲友的一些喝彩,但对于出品和制片人来说,心情是不太一样的。以前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规范,有很多条路可以通向罗马。但现在开始有了一个行业规则,以前大家认为的那种浪漫和幻想性的泡沫全部都破灭了。

中国人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这是传统的大数据和概率统计学。制片能出一个好作品,往往都像开机仪式一样,要祭拜天地上香。王鲁娜进入电影是从《中国合伙人》开始的,是讲述原来自己奋斗过的新东方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里程碑式地对外文化输出,定义了什么是中国好故事。
王鲁娜说,自己做的电影,如何去投国外的电影节,进入到海外市场,应用相匹配的资源理解,去进行整体的把控,同时对内具备跟中国体制和主管部门打交道的一些情商和经验,这些能够给整个片子的天时地利人和带来一定的确定性。
在2018年,王鲁娜投资了哈萨克斯坦电影《小家伙》,这部电影拿了当年的戛纳最佳女主角。引进到中国的时候,人民日报自己写了一个专版,后来国内的丝绸电影节也拿了这部片子当主开幕影片。同年,金鸡奖准备设立最佳外语片奖,只可惜流程没有走完,最终拿了最受欢迎国外影片和最受欢迎国外导演这两个奖。基于时代需求的类型,理解中西方,全球化的语言,这些使电影成为了嫁接的一个官方签证,在完成文化交流属性后,那么剩下的就是解锁国内10亿票房或者5亿+票房的密码。这样的市场化的东西,未必是靠硬性的工业程度,技术和资金盘子来完成的。王鲁娜讲,这个密码我还没有找到。但继续创作,是找到它的唯一路径。




电影《小家伙》剧照
疫情三年,一下子就过去了。她在感慨,一下子我干电影干了十年了,那么下个十年,我还能再争取争取。等到了五十岁,可能就不做这个行当了。在每个时代动态节点里,当一个电影制作人并一直交着学费,是保证自己去拥有更多的确定性,等人心天心风云际会的那一霎,就能看到作品如明月从黑幕和水面上冉冉升起。


德彪西和拉赫马尼诺夫这两个作曲家,特别像姚婷婷入行刚开始的隐喻。一个明亮多彩,有梦幻般的模糊意象,是青春偶像剧里亚麻色头发的少女;一个是厚重的浪漫主义,要连绵不绝地向前喷薄。她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有剧、有长片作品出来,讲述青春,描摹爱情的奇幻和迷茫。直到一个休止符跳了出来,那一年她正在拍摄电影《我在时间尽头等你》。虽然病愈后工作并没有停歇,她又陆续完成了VR电影《时光投影里的秘密》、网络电影《我们的新生活》和电视剧《请叫我总监》,但这一场重病后,人生变奏了。
生病之前,她不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排序里面,身体健康、生活关系要凌驾于拍电影这件事之上。乃至于她昏倒,都是在剧组里面。导演对于年轻人来说,无论男女,一开始都是个梦。对每一个想做导演的人来说,拍出作品去证明自己,走出这一步是一件公平的事。成为导演之后,那么需要的就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同时,也要面对更多的挑战,包括可能合作的人在意见和性情上与自己不是那么合拍这样的压力。

ISSEY MIYAKE 黑色上衣
SHANG XIA 白色半裙
Burberry 黑色高跟鞋
很多女性都比男性拥有更敏感的时间规划,因为职场、家庭还有自己的生理性都是跟时间点客观上挂钩的。姚婷婷说,在30岁之前的工作节奏很快,那时候会觉得有项目找上来是件幸运的事。做完了网剧《匆匆那年》,就一定要拍电影,但总感觉缺那么一点如释重负的松弛。拍上了电影就还会想怎么拍才对得起所有人,自己要变成更成熟的导演。即便这是一个对普罗大众来说都算正常的思维,但带到生活当中都是无形的逼迫和焦虑。她说,这不一定是好事,对你的人生更大的格局,或者是对你自己的身心健康,都不是一个正向的推动。人在处理和面对自己的目标的时候,它是转换成动力还是转换成焦虑,这是很难的课题。
“导演是第一责任人。”如果电影不好看,观众会骂演员会骂编剧,但承担骂名最多的还是导演,所以自己不可以软弱,不能逃避责任,也不能面对困难产生不必要的情绪。合作方合作下来,对她最大的惊讶往往不是,她是一个长相漂亮的女导演,而是姚婷婷真的太能吃苦了。似乎她能扛下所有的事情,一直扛着不吭声,直到她身体没扛得住。“人得知道有的时候有一些事不是你自己能控制的,有的时候是无能为力的。”

在年轻的时候姚婷婷有一种心态,觉得只要愿意吃苦,愿意去解决问题就没有什么是战胜不了的。当运气给了你机会,就一定要好好抓住,要对得起或者是说我一定能克服所有问题。直到她躺到病床上的时候,医生问,你要是想身体好,你能不能换个职业?她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无能为力,在没有办法去实现自己的愿景的情况下,她没办法解决问题了。所以得学会接受,明白不是什么情况都是能被控制和解决的,需要跟不圆满共存,去随遇而安。
她前阵子看了一个纪录片《人生果实》,里面有一句话——我们决定不了生死,那就少一些遗憾。拍电影其实永远会跟预期的样子有偏差,但姚婷婷觉得尽人事之后就不是遗憾。但人生中,就会有这样的遗憾,自己的姨妈去世之前曾一度给她打电话,但由于当时她工作特别忙,想的是改天去回电话,就这么一念之差,没有通上最后的联系。《金刚经》中说,智慧从烦恼中来。这些遗憾和烦恼,促使她成长并得出感悟,你当下能做的事情那就当下去做,你当下能爱的人就当下去爱,不要永远将爱留在明天。
如果说自己的人生能有一些场景,跟电影片段一样,让人那么印象深刻,那么姚婷婷会想到自己动完手术,是在福建的一个医院里,条件其实不是那么好,事出仓促。她在术后等待麻醉过去恢复知觉之前,在一个多人病房里面,有的人呻吟,有的人打鼾,妈妈第一时间飞过来陪伴在病床边,就趴伏在她身边。姚婷婷沉沉地醒来,一下子把妈妈给惊动了,轻轻地唤着她的小名,说你醒了啊。事后她才知道,在术后昏睡的夜里,她妈妈一直在记自己心跳的频率和血氧饱和度。每10分钟记一次。这样的瞬间像跨越了两个人的生命一样长。
策划&编辑/张慧
采访&撰文/苏荣坤
摄影/王天尧 造型/李晓倩
化妆/Renmo 发型/Weidan
制片/C·SIDE @cside_production
造型助理/小房、崽崽
设计/Yan
新媒体编辑/Summer
新媒体设计/CC




-

- 小学数学基础知识点大全 小学数学知识点总结书籍推荐
-
2024-01-09 18:49:14
-
- 陈情令分集介绍电视猫 陈情令电视剧每集的简介
-
2024-01-09 18:47:09
-
- 游击队之歌词曲图片 游击队之歌词曲是谁
-
2024-01-09 18:45:04
-

- 民国1928年什么生肖 1928年是民国时期吗
-
2024-01-09 18:42:59
-

- 7一12岁儿童励志电影免费 7一12岁儿童励志电影动画
-
2024-01-09 18:40:54
-

- 秋葵老了硬了还能吃吗图片 秋葵变硬还能吃吗
-
2024-01-09 13:48:24
-

- 前天晚上做的三明治第二天能吃吗 三明治当天做第二天吃可以吗
-
2024-01-09 13:46:19
-

- 普洱生茶与熟茶的口感有哪些区别 普洱生茶和熟茶哪个口感好
-
2024-01-09 13:44:14
-

- 猕猴桃和西红柿可以一起吃吗 桃和西红柿可以一起吃吗
-
2024-01-09 13:42:09
-

- 绞肉机可以把鱼刺打碎吗 鱼刺用绞肉机能绞碎吗
-
2024-01-09 13:40:04
-

- 饺子皮有一点酸能吃吗 饺子皮怎么会有酸味
-
2024-01-09 13:38:00
-

- 胡萝卜和玉米可以一起吃吗
-
2024-01-09 13:35:55
-

- 黑树莓能吃吗 黑树莓哪些人不能吃
-
2024-01-09 13:33:50
-

- 购买保险的好处 买保险的好处的语句
-
2024-01-09 13:31:45
-

- 凤仙花泡水洗脚可以吗 凤仙花加白醋泡脚的功效
-
2024-01-09 13:29:40
-

- 女生等你表白的暗示,女生等你主动的暗示
-
2024-01-09 02:41:23
-

- 脑瘫的症状表现有哪些(孩子走路姿势异常小心脑瘫,脑瘫都有哪些症状表现?)
-
2024-01-09 02:39:1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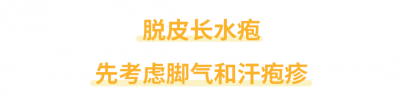
- 脚心长水泡 脚上长出痒痒的水疱,除了挠还能怎么办?
-
2024-01-09 02:37:13
-

- 鸡尾酒调酒配方大全简单(世界十大经典鸡尾酒(附配料及调制方法,建议收藏)
-
2024-01-09 02:35:07
-

- 何首乌的功效与作用 何首乌的功效与作用及食用方法
-
2024-01-09 02:33:02



 门口放什么能克邻居(对门邻居一旦在门上挂这个玩意,你马上让他拆了,否则倒霉
门口放什么能克邻居(对门邻居一旦在门上挂这个玩意,你马上让他拆了,否则倒霉 罗汉肉是什么部位 罗汉肉是什么部位的肉,吃了健康吗
罗汉肉是什么部位 罗汉肉是什么部位的肉,吃了健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