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庭笈-被俘改造生活
郑庭笈-被俘改造生活
郑庭笈,广东省海南岛文昌人,生于1905年,原为国民党第四十九军中将军长,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役中被俘。1959年12月4日获得特赦,曾任全国政协委员、文史专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
每当他回想起在战犯管理所的生活时,总会说:“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但在人的一生中,也许会产生根本的转折。十一年的改造生活,使我好像从血雨腥风中走来,蹒跚地走到荆棘小路的尽头,终于看到了康庄大道,找到了我的人生归宿。”
1948年9月,辽沈战役在辽西走廊拉开序幕。当时我任国民党第四十九军军长,该军编入辽西攻击兵团,廖耀湘任兵团司令。
东北解放军主力(由林彪、罗荣桓率领)包围了锦州范汉杰兵团,锦州危在旦夕。廖耀湘兵团奉命由沈阳沿北宁路西进增援,但解放军已捷足先登,我们遂又改向营口,可计划又遭失败。10月26日,奉卫立煌命令向沈阳撤退。途中在大虎山附近被解放军主力包围,各部失去联络,各自为战,陷于解放军四面炮火交叉射程之下,如瓮中之鳖,东逃西跑,互相践踏,人仰马翻。我带领军指挥所人员和第一九五师师长罗莘求,仓皇跑到第一九五师一个步兵团团部里,在李家窝棚被解放军包围。27日激战整日,村口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我们几次试图突围都没有成功,人员死伤过半。我和罗在掩蔽部里挨到午夜时分,此时四面炮声沉寂,我们带领特务连突围,盲目地向沈阳辽河方向前进,走有二十华里左右,于28日拂晓,撞到解放军第七纵队某师工兵连哨所,随即被俘。当日廖耀湘兵团全军覆没。大虎山地区已没了激烈的枪炮声,各村庄成了国民党被俘官兵收容所。30日,我、罗莘求和新六军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罗英同被送到黑山县北镇收容所,在那里我遇到了新一军副军长兼第三十师师长文小山,该军第五十师师长杨温、副师长陈时杰,新三军参谋长李定陆、该军第十四师师长许颖、第五十四师师长宋邦纬、暂编第五十九师师长梁铁豹,第六军第一六九师师长张羽仙,第四十九军第一○五师师长许玉桢等,各师、团长都在那里集中。后来又知道廖耀湘和新编第六军军长李涛、第七十一军军长向凤武也被俘了。起初,廖耀湘还假称是第九兵团书记官,终被揭发。
此时,我完全陷于绝望的阴雨凄风里。战役失败的后果我是明白的:锦州解放,长春投诚起义,廖耀湘兵团全部被歼,解放沈阳指日可待;东北解放后,几十万解放军入关,平津、华北恐怕在劫难逃,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打败仗是军人的耻辱,而这一耻辱的最大内涵是:我半生的戎马生涯以失败告终了!将来会怎样呢?
一、北国之家
我生于椰林碧海的海南之乡,广州黄埔军校是我人生的起步点,从此出生入死,转战南北,而今在这林海雪原的北国,我面临着人生的转折……
正值北方寒冷的冬天,我坐在隆隆前进的火车上,望着车窗外朦胧的大地、纷飞的雪花,心情难以名状。我仿佛看到老母又在为我敬神祈祷,看到了她那哭干了泪水的双眼、满是皱纹的蜡黄的脸;想起儿时家境不宽裕,平时靠吃白薯、野菜、碎米汤度日,母亲却常常拿张棕叶包些米,放在汤里煮米饭团独给我吃,盼我长壮些,将来好有出息。进了黄埔,我从见习官到排长、连长,经南征北战,直到当了军长,母亲日日为我祷告,求神保佑。我只盼世泰民安,早日解甲归田,以尽孝道,没想到结局如此之惨。
还有爱妻,随我颠簸,为我担忧,此刻我在北国,她却在千里之外的南方海口,膝下三女二儿,将来以何为靠?莉娟呀,我对不起你,多保重吧!
……
这时我油然感到一股刺骨的寒意,不禁打了个冷战,身体蜷得更紧。想到被俘后解放军第七联队司令员找我谈话,要我解除顾虑,说:“放下武器,我们就是朋友了。”并要我换上解放军的棉大衣防寒,我拒绝了。只待一死,冷又何妨?况且临死穿着国民党军服也算表示对党国尽忠到底了。天气冷,我的心更冷呀。
1948年11月11日,我们到达了哈尔滨,到东北解放军官第五团集中。
凌晨下了火车,徒步到南岗。算幸运,雪在夜里就停了,太阳露了头,照着银白的大地,风也收敛了许多,一切显出难得的静美。而我不免怅然,这大自然风光已不属于我,我是罪犯!谁知这是不是上天对我们这些将入地狱的灵魂所表现出的一丝怜悯呢。唉!我倒更愿葬身大海,漂流到自己的故乡!我鼻子似乎有点发酸,但没有泪水,只待一洒热血了。
东北解放军官团,设在哈尔滨南岗原日本陆军医院,是楼房,有围墙,院里空地很大,环境优美清静。我走进大门时脚步并不轻松,首先进入我眼帘的是许多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在院里散步,看到他们红光满面,精神抖擞,我颇为吃惊。就这样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开始了战俘生活。
解放军官团分有高级一队、高级二队、中级队。团部有团长、政委,队里有队长、管理员等。高级一队主要是国民党军、师长以上被俘人员,高级二队是副师长、团长等被俘人员,中级队按兵种有营长以下人员。当时凡军医、工兵、炮兵、通信兵、驾驶兵等都征求参军,不愿参军的,给路费回原籍。
我们的生活待遇分为小灶和中灶,高级队吃小灶,有鱼有肉,比中级队生活好。几位兵团司令:范汉杰、廖耀湘、卢浚泉、周福成、李仙洲等都单独住一个房间,有炊事员单独给他们送饭。李仙洲当时是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在山东莱芜战役被俘,与第七十三军军长韩浚、整编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等转送到哈尔滨。
是战争把我们这些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在这里,大家都不觉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但又是各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都竭力掩饰忐忑的心情。
这是我的第一个战俘之家,我称之为“北国之家”。
冰雪在融化,心灵在复苏,在真理面前我不能视而不见,在命运面前我不能永远做奴隶,我终于做出了选择……
鏖战奔波后的平静并未使我轻松,反而寝食难安,在心灵的天平上一边是死亡的铅锤,一边是生存的薄雾。共产党优待俘虏,是真是假?虽然眼见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下级军官、军医、军需等得以放生者确实大有人在,但对国民党高级军官呢?现在的情况是国共两党誓不两立,想得到优待,实为幻想矣!不过对共产党我也无可指责,过去清党当中不也提出过“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的杀戮政策吗?我只有诅咒自己的命运了。
有一个问题是我不能不考虑清楚的:我们败在哪里?我不由想起有些国民党将领,提到共产党的打法时,总以戏谑嘲笑的口吻,将集中优势兵力诬称为“人海战术”,而我们岂不正葬身于这人海之中吗?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兵力多少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国民党将领总好称自己的“八百万”军队,殊不知共产党的麾下是亿万中国民众。真心实意替国民党打仗的人从哪里来?我开始怀疑了。
“政为舟,民为水;载舟之水,亦可覆舟。”在中国,国民党执政,民心尚不可顺,而共产党在野,却能一呼万应,就是这个道理。所谓“顺民者昌,逆民者亡”也。“我们的失败是必然的。”我在心里不无怅惘地说。
当时解放军官团的主要任务是写信、写广播稿,劝国民党军弃暗投明。我到解放军官团的第三天,团里何政委就找我谈话,要我写信给当时在北平的国民党第九十四军军长我的哥哥郑挺锋,告诉他我被俘经过,劝他早日放下武器。命运就是这样富有戏剧性,9月19日我经北平去南京时,还在他家见到他,同桌畅饮,而事隔两月,我已是笼中之鸟,他恐怕也将为瓮中之鳖了。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能总做命运的奴隶,我们兄弟难道只能在高墙之内再见吗?这太可怕!思来想去,我拿起了笔,写了下面这封信:
锋哥:
十月二十八日我在辽西打虎山被解放,十一月十一日到达哈尔滨解放军官团高级队学习,一切均胜于前,请放心。弟来哈后,回顾前事,感触万端。犹忆二十年前,我们都因受着大家族和地主的压迫,辍学而走广州,入黄埔参加革命工作。当时革命军因实行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主张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者联合起来,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所以能以少数革命部队,战胜了北洋军阀集团。但以后国共合作不幸为蒋介石所破坏。蒋介石不扶助工农,反而压迫工农;不实行联俄、联共政策,反而实行所谓反帝反共政策,变为袁世凯第二;蒋介石使曾与共产党合作革命的国民党,变为反动派把持包办的反共反革命党,陷国家民族于半殖民地地位。
我现在最痛心的,就是二十年来,我们竟跟着蒋介石走,做了许多反共反人民的坏事,完全和我们初入黄埔时的志愿相违背,而未能迷途知返,早日向人民请罪。现虽蒙解放军宽大待遇,未予惩处,但自己究竟不能不受良心责备。试想二十年来,在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之下,我们哪一天不是醉生梦死?哪一天感到了人生的意义和乐趣?但一看解放区,则一切完全相反,处处觉得光明、愉快、有朝气,与大革命时代的黄埔相比,确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不但工农兵学商各界人人安居乐业各得其所,就连被解放的国民党官兵,也好比恢复了生命一般。同是一个士兵,替国民党打仗时就不爱打,而替解放军打仗就爱打了。这看来是怪事,却是千真万确的事。此次义县被解放的士兵,不到三五天的工夫,就参加了锦州攻城战,而且有许多战士立了战功。还有被解放的军官,在军官团中那种勤学情形实为弟生平所未见,亦为吾哥所决难想象。凡此种种,均使弟对过去愧悔交集,对将来充满希望。
弟今既已亲历一切,不能不念手足之情,向吾哥沥诚倾吐,以冀吾哥勿蹈弟等在辽西之覆辙。
国民党统治的形势,如以东北为首,华北为胸,华中为腹,华南为脚,则今首已斩断,胸部惟存平津几座孤岛,腹部之济南、郑州、开封、徐州均已先后解放,仅存汉口、蚌埠等少数据点。试问只有民心离弃,民变蜂起之华南,究竟尚能持久几时?国民党在全国大势已去,平、津迟早是要解放,多守几天少守几天,又有什么很大的差别?长春固守几月,结果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终于六十军起义,郑洞国及新七军投诚。北平今日已处大军重围,更非长春只有几个独立师包围所可比拟。要守几个月是不可能的,北平守军之训练装备远不如辽西之新一军、新六军,但此两军作战不到六十小时即完全被歼。在东北人民解放军今年秋季攻势中,短短五十二天,即解放了全东北,国民党四五十万部队全部覆灭。今东北人民解放大军源源入关,会合华北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排山倒海之势,扫荡华北国民党军之残余,试问谁能抵抗?必欲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不过徒作无谓牺牲,于己于人,有何裨益?平津必然变为锦州、沈阳第二,傅作义必然变为范汉杰或卫立煌第二,大批军队投诚的投诚,被歼的被歼。到了那种地步,再回头已晚了。
蒋介石的失败已经注定了,任何挣扎,均属徒劳。语云:“顺天者昌,违天者亡。”蒋介石既然违背了广大人民的利益,逆天而行,终必灭亡。解放军忠实于广大人民的利益。一举一动均以国利民福为依归,顺天而行,必然胜利,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孙中山先生说:“凡事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这岂非今天人民解放战争的写照吗?时势如此,望吾哥明辨大局,早日率部投诚,以免牺牲多人生命。我兄弟亦可早获团聚。弟现在确已大彻大悟。吾哥勿谓弟自丧立场,替共产党说话。实则这些话过去我不懂得说,也不想说不敢说,现在我懂得了,因此也就敢想和敢说了。现平津大战,爆发在即,时机迫切,望断然行之,为祷,为祝。
此颂时绥
庭笈弟手启
于哈市解放军官团十一月十六日
这封信是于11月16日晚8时由高级队队长陪我乘吉普车到哈尔滨广播站广播的。17日《东北日报》首版全文发表。当时在解放军官团反响强烈,大家都争看当日报纸。当然,解放军官团的领导对我颇为满意。20日谢团长亲自陪我去新华书店,赠给一本精装《毛泽东选集》,有记者给我拍了相片,而后又上饭馆吃饭,看电影。看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一派和平景象,我似乎已置身于他们当中,忘记了自己是战俘。这是我战俘生涯中难忘的一天,这一天我看到了一丝生存的莹光,冰冷的心中产生了暖意。
随即我又向在海南岛海口市的妻子冯莉娟播音,要她保重,不要去台湾,“我不久就要回去。”这最后一句是谢团长嘱咐再三我才说出的。

郑庭笈
-
- 他全家性命危在旦夕,连续被50多个国家拒签,直到来中国总领馆
-
2024-12-20 16:48:30
-

- 印度极力反对,中国价值高达4万亿的红旗河工程,真的可行吗?
-
2024-12-20 16:46:15
-

- “内地音乐教父”张亚东:高圆圆疯狂倒追,瞿颖不婚陪他11年
-
2024-12-20 16:44:0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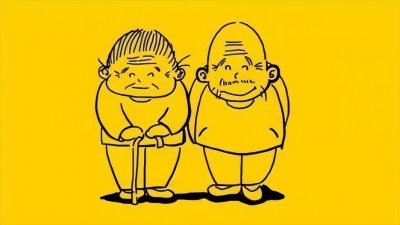
- 孝敬父母的名人故事
-
2024-12-20 16:41:45
-

- “艳星”舒淇:因年少时的错误抉择而后悔不已
-
2024-12-20 16:39:30
-

- 徽常文化圈 - 吴斯:一个女导演的“匠心”养成
-
2024-12-20 16:37:1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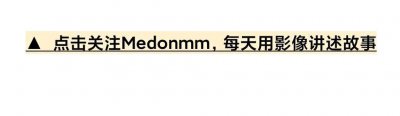
- 在美消失的北大女学生章莹颖:不负责任的美国政府至今未给说法
-
2024-12-20 16:35:00
-

- 长相甜美身材性感火辣的兮妹儿
-
2024-12-20 02:19:21
-

- 红米新品发布会 Redmi Note 8 Pro 正式亮相:对标友商 3000 元旗舰
-
2024-12-20 02:17:06
-

- 表情包上线!白百合嘟嘴瞪眼扮鬼脸,学龅牙兔神还原,捂嘴大笑
-
2024-12-20 02:14:51
-

- 宝藏作者「栖见」七本 超火合集,每一本都是清新高甜
-
2024-12-20 02:12:37
-
- 新生代演员傅杨杨 花样青春花样年华
-
2024-12-20 02:10:22
-

- 台山汽车总站
-
2024-12-20 02:08:07
-

- 诗词日历 - 和子由四首·送春
-
2024-12-20 02:05:52
-

- lady first 啥意思?在英语里常用吗?大家又犯错了!
-
2024-12-20 02:03:37
-
- Ivvi新机“小骨”亮相 赵丽颖代言
-
2024-12-20 02:01:23
-

- 熹妃传时装传记高分攻略汇总
-
2024-12-20 01:59:08
-

- 男人为什么占有欲那么强?
-
2024-12-19 21:15:18
-

- 川菜C0215子姜鸭做法
-
2024-12-19 21:13:03
-

- 2000泰铢 泰落地签费用涨价了?
-
2024-12-19 21:10:49



 省长工资的简单介绍
省长工资的简单介绍 鄂州地区抢先一步,葛店率先并入武汉,下一个会是哪个城市?
鄂州地区抢先一步,葛店率先并入武汉,下一个会是哪个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