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哲学史丨施杜里希:托马斯·阿奎那
世界哲学史丨施杜里希:托马斯·阿奎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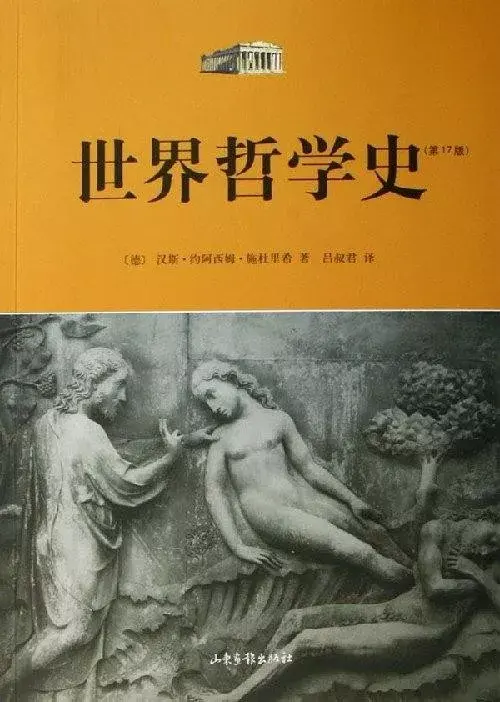
生平和著作
位于罗马和那不勒斯之间,离阿奎那不远的地方,有一座被称作罗卡塞卡的城堡,1224与1225年交接之际,托马斯出生了,他是朗多尔夫·阿奎那伯爵的儿子,这位伯爵是霍亨施陶芬皇族的亲戚。五岁时,托马斯被送进离家不远的卡西诺山上的本笃会修道院接受教育。在他还是个男童时,他就进入那不勒斯大学学习“自由艺术”。十七岁时,他加入了多明我修会。第二年,该修会就派他去巴黎继续深造。因为他家里人不同意他的决定,在前往巴黎的途中,托马斯被他的兄弟劫持了,并被押送回他父亲的城堡里。但是托马斯从事神职的决心已定,他坚韧不屈。他成功地从囚禁他的家里逃脱出来。他来到巴黎,并和大阿尔伯特相识。阿尔伯特成了他的老师。托马斯终生追随着他敬爱的老师,矢志不渝。经过三年的学习之后,阿尔伯特偕同托马斯一起前往科隆,在那里,托马斯又在老师的指导下继续学习了四年。1252年,他重新回到巴黎,并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他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教学活动中去,托马斯对教师这个职业评价很高。他把神学教师对教徒的精神指导比作建筑师的事业:一个建筑师事先会在头脑里设想出一个计划,然后他再按照这个计划建造他的建筑,一个神学教师在对教徒进行指导时,他事先也要自己的头脑里有一个计划。后来,托马斯回到他的故乡意大利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在那里担任奥尔韦托教廷里的神学教师,并且结识了他的精通语言的教友莫尔贝克的威廉。威廉曾经把大量的希腊著作翻译成拉丁语,其中主要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在这里,托马斯比较细致地熟悉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的老师阿尔伯特基本上是依据从阿拉伯语转译的亚里士多德著作译本从事研究的,与那些译本相比,威廉的译本要更胜一筹。
1269—1272年,托马斯第二次逗留巴黎期间,他的学术生涯达到了一个顶点。托马斯成为最受欢迎的神学教师。遇到引起争论的问题,人们最后都来听取他的意见,在许多论辩中,他说的话最具权威性。后来,他所属的修会把他召回那不勒斯,让他负责组建修会大学的神学系。1274年,教皇又委任他参加在里昂举行的宗教全会。在前往里昂的途中,在离普利维诺不远的佛萨诺瓦修道院里(这个地方介于那不勒斯和罗马之间),死神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由于他性格温和而正直,人们称他是“天使博士”(doctor angelicus)。
托马斯著述颇丰,在这一点上,他并不亚于他的老师阿尔伯特。十六世纪末,他的著作全集首次在罗马和威尼斯出版,当时就已经达到十七卷之多。十九世纪中期出版的意大利文版托马斯全集共有二十五卷,十九世纪末出版的法文版托马斯全集则多达三十四卷。
有一套附有评注和手稿鉴定的托马斯著作集,收集在其中的文章被确定为托马斯的著作真品,这套文集将托马斯的著作做了如下划分:
1.亚里士多德注释。包括十二卷,是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解,涉及《后分析篇》、《伦理学》、《形而上学》、《物理学》、《政治学》、《论灵魂》、《论天》、《论自然物的形成与消失》等。
虽然托马斯对亚里士多德的注释没有像阿尔伯特所做的那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阿尔伯特是第一位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做全面注释的人,但是,与阿尔伯特相比,托马斯的工作则更为科学,因为他能够利用更为详尽的资料,而且与阿尔伯特不同,托马斯更能够将亚里士多德的原文与自己的注解文字明确地区分开来。此外,托马斯的拉丁文水平比阿尔伯特更加娴熟,因为作为一个意大利人,他的母语与拉丁语更为接近。
2.哲学著作。其中主要有《论理智的统一性——反对阿威罗伊主义者》。这是托马斯针对十三世纪时在巴黎大学影响较大的一个思想运动而写的,这个运动的代表人物是西格尔·冯·布拉邦特(约1235—1281)。对这个思想流派来说,阿拉伯人阿威罗伊对亚里士多德所做的解释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即使他的话与基督教教义相违背,他们也表示赞同。众所周知,阿威罗伊教导说,世界是永恒存在的,而不是被创造的,此外他还说,物质本身就潜藏着所有的变化形式;他也否认个体灵魂的不朽性;他在哲学中找到了更高的和更纯洁的真理。这个学派被称为拉丁化的阿威罗伊主义,或阿威罗伊式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托马斯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正如托马斯所期待的,这个学派遭到了教会的抵制。西格尔与托马斯之间的争论是中世纪哲学中众多的激烈争论之一,类似的争论在这一时期基本上就没有间断过。在我们这一部入门性的著作中,一一列举这些争论是不可能的,当然共相之争是个例外。
3.神学大全。其中包含托马斯的两部重要著作:对彼得·朗巴尔德的《箴言集》的注释,以及托马斯自己并未完成的《神学大全》。
4.问题集。这是大学里定期举办的神学争论问题的汇编。
5.关于基督教教义的短文。共十二篇。
6.论辩集。这是托马斯为维护基督教信仰而写的辩护词,包括:《反异教大全》,主要是针对阿拉伯人;《论信仰的基础》,针对萨拉逊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希腊人的迷误》。
7.法律、国家和社会哲学著作。共六篇,其中有《论君主统治》和一篇论述如何对待犹太人的文章。
8.论修会事务和修会规章的文集。
9.对圣经的诠释著作。
其中的两部较为重要的著作是:《神学大全》,写于1266—1273年间,托马斯没有完成,由他的一位后继者增补;《反异教大全》,也被称为《哲学大全》,写于1259—1264年。
托马斯著作的特点是条分缕析和脉络分明。托马斯特别强调,“教师不仅仅要向具有一定水平的人,而且也要向刚刚入门者传授基督教真理,”因此,他尽可能地使他的文章简单、清晰和一目了然,而这正是他那个时代的那些箴言集和神学论辩文章所欠缺的。对托马斯来说,精确的表达和避免引起歧义比华丽的辞藻更为重要。
知识与信仰
托马斯对知识和信仰的领域做了划分。首先关于知识,他的坚定不移的信念是,存在一个合乎规律的现实世界,而且我们也能够认识这个世界。这也就意味着,他确信人能够获得真正客观的知识,因而他也就否定了如奥古斯丁的那种哲学,即认为现实世界只是思想的人的精神产物,并且试图将精神限定于对它自己的形式的认识。
在托马斯看来,“认识的对象是和认识能力相应的。认识能力有三等。一种认识能力是感觉,它是一个物质机体的活动;因此,每一感觉能力的对象都是存在于有形物质中的一种形式;这样的物质是个体化的本原,所以感觉部分的每种能力所取得的知识只能是个体的知识。另一等认识能力既不是一个物质机体的活动,也和有形体的物质没有任何关系。这就是天使的理智。这种认识能力的对象是脱离物质而存在的一种形式。天使虽然认识物质事物,但也只有从非物质事物(或从自身、或从上帝)的地位去认识。再一等是人类的理智,处于中间地位。它不是一个机体的活动,而是灵魂的一种能力。灵魂本是身体的形式。所以,它在有形物质中去认识单个地存在着的形式,是适当的。不过,不可认为这形式就存在于这一单个的物质中。从个别物质中去认识其形式而不把它当作存在于那样的物质中,这就是从表现为影像的个别物质抽出其形式。所以,我们必须说:我们的理智是用对种种影像进行抽象的方法来了解物质事物,而我们正是通过这样了解的物质事物获得某些非物质的事物的知识,反之,天使却是通过非物质事物来认识物质事物”。
如果说我们的认识是客观的和真实的,那这还不够。在哲学和形而上学的认识世界之上,还有一个超自然的真理的世界。单靠自然的思维能力,我们不可能认识这种超自然的真理。在这个问题上,托马斯与早期经院哲学家如厄留根纳和安瑟尔谟观点相异,后者曾经试图用理性来审视和解释整个基督教教义。基督教信仰的真正秘密(上帝的三位一体、上帝的人格化和道成肉身)恰恰不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在托马斯眼里,这些都是超自然的真理,我们只能虔诚地把它作为神圣启示来接受。
在知识和信仰这两个范围内,永远都不会存在矛盾。虽然基督教的真理是超越理性的,但它不是违背理性的。真理只能是一个,因为它来自上帝。倘若有人站在理性的立场上针对基督教信仰提出异议,那么它自身必然也是违背理性的最高思维原则的,因此我们可以用理性的工具对其加以驳斥。这也正是托马斯坚持不懈地在他的论辩性著作中针对异教徒和基督教异端分子所做的重要事情。
此外,也有关于上帝的真理,我们的理性能够认识这种真理,比如,上帝的存在,比如只存在一个上帝。当然,由于缺乏天赋,由于懒惰,而且还由于必须花费很多精力用于完成一些琐碎的人生事务(比如要维持自己的生存和照料家庭),大部分人都没有能力专心致志地思考问题并去接近真理。所以,神圣智慧将那些本来能够被理性所认识的信仰真理也变成超自然的启示。
倘若某些宗教真理能够被理性所认识,那么哲学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可以为信仰和神学服务。此外,哲学还可以用来证明那些针对信仰提出的理由是错误的和站不住脚的。当然,哲学的任务也仅限于此,它不能证明超自然的真理,而只能对那些自相矛盾的论据加以驳斥。“我首先想提醒你,在与那些无信仰的人辩论的时候,你不要试图用具有说服力的理性理由去证明信仰真理。这会损害信仰的崇高性……我们的信仰不能用有说服力的理性理由加以证明,因为它是超越理性的,我们的信仰也不可能被有说服力的理性理由所推翻,因为它是真实的,因而它不可能与理性相违背。基督教的辩护士们与其努力用哲学来证明信仰真理,倒不如通过驳倒对立双方的异议,从而阐明天主教信仰不是错误的”。
在这方面,作为服务于神学目的的工具,经院哲学的作用达到了它的顶峰。
上帝的存在与本质
在托马斯看来,上帝的存在是可以通过理性加以证明的。不过,托马斯对坎特伯雷的安瑟尔谟的那种本体论的上帝之证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安瑟尔谟是想从上帝的概念本身推导出上帝的存在。托马斯认为,“上帝存在”这句话并非一种自明的真理,也不是人的天赋真理。它必须首先被证明。《神学大全》里按顺序列举出了证明上帝存在的五种理由,我们摘录如下:
上帝的存在,可从五方面证明:
首先从事物的运动或变化方面论证。在世界上,有些事物是在运动着,这在我们的感觉上是明白的,也是确实的。凡事物运动,总是受其他事物推动;但是,一件事物如果没有被推向一处的潜能性,也是不可能的……一件事物不可能在同一方面、同一方向上说是推动的,又是被推动的。如果一件事物本身在动,而又必受其他事物推动,那么其他事物又必定受另一其他事物推动,但我们在此决不能一个一个地推到无限。因为,这样就会既没有第一推动者,因此也会没有第二、第三推动者。因为第一推动者是其后的推动者产生的原因,正如手杖动只是因为我们的手推动。所以,最后追到有一个不受其他事物推动的第一推动者,这是必然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个第一推动者就是上帝。
第二,从动力因的性质来讨论上帝的存在。在现象世界中,我们发现有一个动力因的秩序。这里,我们决找不到一件自身就是动力因的事物。如果有,那就应该先于动力因自身而存在,但这是不可能的。动力因,也不可能推溯到无限,因为一切动力因都遵循一定秩序……因此,有一个最初的动力因,乃是必然的。这个最初动力因,大家都称为上帝。
第三,从可能和必然性来论证上帝的存在。我们看到自然界的事物,都是在产生和消灭的过程中,所以它们既存在又不存在。它们要长久存在下去,是不可能的。这种不能长久存在的东西,终不免要消失。所以,如果一切事物都会不存在,那么迟早总都会失去其存在。但是,如果这是真实的,世界就始终不该有事物存在了。因为事物若不凭借某种存在的东西,就不会产生……不过,每一必然的事物,其必然性有的是由于其他事物所引起,有的则不是。要把由其他事物引起必然性的事物推展到无限,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有某一东西:它自身就具有自己的必然性,而不是有赖于其他事物得到必然性,不但如此,它还使其他事物得到它们的必然性。这某一东西,一切人都说它是上帝。
第四,从事物中发现的真实性的等级论证上帝的存在。……世界上一定有一种最真实的东西,一种最美好的东西,一种最高贵的东西,由此可以推论,一定有一种最完全的存在。……因此,世界上必然有一种东西作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得以存在和具有良好以及其他完美性的原因。我们称这种原因为上帝。
第五,从世界的秩序(或目的因)来论证上帝的存在。我们看到:那些无知识的人,甚至那些生物,也为着一个目标而活动;他们活动起来,总是或常常是遵循同一途径,以求获得最好的结果。显然,他们谋求自己的目标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计划的。但是,一个无知者如果不受某一个有知识和智慧的存在者的指挥,如像箭受射者指挥一样,那他也不能移动到目的地。所以,必定有一个有智慧的存在者,一切自然的事物都靠它指向着他们的目的。这个存在者,我们称为上帝。
显而易见,托马斯的这些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是以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的学说为依托的。在解释上帝的本质方面,托马斯试图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一条介于人格化的上帝观念和新柏拉图主义的上帝观念的道路。我们关于上帝的认识有三个特征:首先,它是一种间接的认识,也就是通过上帝在自然中的影响来认识上帝;其次,它是一种类推的认识,也就是依据造物与被造物之间的相似性关系推论出上帝的存在;第三,它是一种整合的认识,我们只能从各个不同的侧面逐步地认识上帝无限完美的本质。总之,这种认识是不完善的,但它毕竟是一种认识,它会教导我们,把上帝看作一种以自身为原因的完美存在。
神圣启示告诉我们,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在托马斯看来,创世是只有通过启示才可认识的真理)。在创世中,上帝实现了他的神圣理念——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柏拉图理念论的再现,当然是以一种改变了的形式。
人与灵魂
我们掠过托马斯的宇宙学理论(托马斯坚持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而直接转向他的心理学理论,这也是他的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对托马斯来说,人的灵魂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的对象。在他的许多著作中,他都讨论过人的感情、记忆、个体心灵的能力、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人的认识。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即物质是被动的,形式是主动的和起作用的原则)仍然是托马斯的理论基础。灵魂是赋予一切生命现象以形式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应用到人身上也就意味着:“思维活动的原则,理性灵魂是人的肉体的本质形式。”托马斯解释说,人的灵魂是非物质的,也就是说,它是非物质的纯粹形式,是一种纯粹精神的不依赖于物质的实体。由此便产生了它的不可摧毁性和不朽性。由于灵魂是不依赖于肉体的独立实体,因此它不会随着肉体的消亡而消亡,并且作为纯粹的形式它也不可能自我毁灭。人对永生的渴望并非纯粹臆想,对托马斯来说,这正好为灵魂实体的不朽性提供了证据,在这一点上,他与阿威罗伊主义者不同,因为他们只承认超个体的灵魂的不朽性。
在个别灵魂力量或能力问题上,托马斯仍然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有植物灵魂,它有代谢和繁殖能力;也有动物灵魂,它有感官知觉、欲望和自由活动能力。而在人那里,除了以上这些能力之外,他还有理智能力,即人的理性。托马斯赋予理性以绝对优先地位,理性高于意志。因此,托马斯主义的灵魂和认识理论是理性主义的。在心理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作为多米尼克教徒的托马斯的观点与同一时期的圣方济各修士们的观点是截然对立的。圣方济各修士的神学理论是以奥古斯丁和柏拉图的学说为依据的,他们强调人的认识的主动性特点。而托马斯则以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为依据,强调认识的被动的和接受的特征。他认识到,认识主体与被认识的客体之间存在相似性。如果心灵中的形象与现实达成一致,那么也就获得了正确的认识。
那么如何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呢?对于这个问题,托马斯给出的答案和亚里士多德给出的一样:并非通过分享神的观念(或回忆神的观念),而只是通过人的感官经验。因此可以说,托马斯是个经验主义者。我们所有的认识材料都来自我们的感官。当然它们还只是材料而已。我们的理智将对这些材料做进一步的处理。感官经验只向我们显示个别事物。但是,理智的真正对象则是寓于个别事物之中的本质。为了认识这种本质,精神必须借助于“想象”。在这里,康德的认识论已经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预先被表达了出来,根据他的理论,认识产生于正在形成中的形象,这些形象是借助于人心灵中的思维和直观形式并通过感官知觉而获得的现象。剩下的问题只是,“想象”在感性直观的继续发展中是如何进行的,我们的认识的哪些部分来自感性,哪些部分来自我们自己的心灵的一般形式和特性。
紧接着托马斯的灵魂和认识理论,我们再来看他的伦理学思想。托马斯说:“要获得幸福,人必须知道三件事情:第一,要知道他信仰什么;第二,要知道他渴望得到什么;第三,要知道他应该做什么。”
作为道德行为的前提,托马斯强调了人的意志自由。在这里,托马斯的观点与奥古斯丁以及圣方济各修会的神学理论也是截然对立的。在内心深处,托马斯接近于一种决定论。关于人的具体德性,托马斯吸收了希腊的四种传统的基本德性,即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并附加上三种基督教的德性:信、望、爱。托马斯的伦理学思想结构是极其复杂的,但是他的基本思想却很简单:“理性是人的本性。凡是违背理性的事情,也必然违背人的本性。”“只要他是人,那么人的至善就在于:理性能够在认识真理中获得完善,人的欲求要以理性为准绳。人之为人,就因为他能够掌握理性。”
“一个人具备好的认识力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个好人,要成为一个好人,他必须具备好的意志。”
“沉思的人生要高于庸碌的人生,倘若一个人能够放弃掉一部分他对沉思的爱好,而对他的邻人的幸福做点事情,那么他就能够更好地实现上帝的意志。”
“爱朋友是好的,因为他是朋友,爱敌人则是不好的,只要他还是敌人。但是,假如他是上帝的孩子,那么爱敌人也是好的……把朋友当作朋友来爱,和把敌人当作敌人来爱:这似乎有些矛盾。但是,爱朋友和爱敌人,假如两者都是上帝的孩子:这样就不矛盾了。”
“就我们自身而言,认识比爱更重要;因此哲学家将人的认识品性置于他的道德品性之上。但是若考虑到超出我们自身以外的事情上,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上帝时,那么爱就比认识更为重要。由此说来,爱高于信仰。”
政治
作为坚定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阿尔伯特和托马斯都非常关注现象世界。但是他们两人的兴趣却又分为两种不同的方向:阿尔伯特更为关注的是感性世界,托马斯更为关注的则是道德世界,即国家。若在今天,我们会说,阿尔伯特更像一个自然科学家,而托马斯则更像一个人文科学研究者。阿尔伯特对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著作未作任何评论,而托马斯对这一领域则做了非常深入的探讨。和希腊人一样,托马斯也认为,人完全是处于社会和国家秩序之中的。下面的话就表明了他的这一立场:“倘若一个人对公共利益漠不关心,那么他就不可能是一个好人。”“一种德行涉及公共利益越多,这种德行就越高尚。”
托马斯直接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国家学说,而且托马斯也是西方世界里第一位对国家理论给予如此高度重视的人。在这方面,他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与奥古斯丁的思想结合到了一起。和亚里士多德一样,托马斯也认为人是一种政治动物,是一种社会动物。因此,国家秩序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一个人与许多人共同生活在一起,那么,人与人之间就必须有某种起制约作用的东西。这么多人生活在一起,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愿望,都自私自利地只关心个人的利益,而这时若没有一个人能够以社会的共同利益为己任,那么人类社会将会是一片混乱,这就像人的肉体或任何一种有生命的动物一样,如果在他的体内没有一种起主导作用的、能够顾及到身体的各个器官的共同利益的力量,那么他就不可能存活。”因此,在托马斯看来,一种社会权威就是必要的。由于人在本性上是社会动物,而这种本性是上帝所赋予的,所以,如《圣经》所言,上帝也是统治阶层的倡议者。
托马斯遵循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也将国家形式区分为君主政治、贵族政治和“共和”政治以及与之相对应的退化形式僭主政治、寡头政治和民主政治。在这些国家形式中,托马斯更喜欢君主制。对此他有一种理想的观念。国王在国家里的地位必须像灵魂在身体内和上帝在世界内的地位一样。一个好的和正义的国王的统治必须以上帝对世界的统治为榜样。“如果一个统治者能够很好地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国家谋福利,这就是一种至善,如果他滥用自己的权利,那么这就是一种极大的罪恶。”一切统治形式中最坏的形式就是僭主政治。如果僭主政治成为国家的政体,那么也应该建议它的人民要忍耐,因为暴力革命往往会带来更为严重的恶果。
因为托马斯将国家看作是一个大的道德实体,所以他认为国家的任务就是要使它的人民过一种正直的和合乎道德的生活。这样一种生活的最重要的前提就是维护和平。第二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使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但是,在和平和富裕中的、合乎道德的生活并不是人生的最终目的。人生的最终目的是获得极乐至福。引导人们获得这种极乐至福,这不是世俗统治者的职责,而是教会的职责,也就是神父的职责和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罗马教皇的职责。因为教会的职责高于国家的职责,所以世俗世界里的国王要服从于教会的统治。也就是说,托马斯非常明确地认为,只要尘世的事物对于人的超尘世的目标起作用,那么世俗权力就必须服从宗教权力。
托马斯的意义
“智者的责任就是:整理。”托马斯·阿奎那的毕生事业也可以用这句话来概括。整理、区别、划分——将不同的东西按照他们各自的内在价值加以归类整理,这就是他的著作的伟大和意义之所在。
托马斯过早地去世了,紧接着,在修会内部和整个天主教界,人们围绕托马斯主义的地位问题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反对他的声音主要是来自信奉奥古斯丁哲学的方济各修会神学家们,托马斯在世的时候就与他们展开过激烈的辩论。托马斯去世三年以后,巴黎的大主教对托马斯的几种理论作了公开判决。但是托马斯的学生满怀对老师的崇敬和爱戴,还是坚持不懈地继续贯彻着他的思想。托马斯过去的老师大阿尔伯特比托马斯活得时间长,他称托马斯是“教会的一线光明”。
托马斯主义成为多明我修会的正统哲学。1322年,教皇承认托马斯是圣徒。历史上许多重要的教皇都对托马斯的学说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致力于传播他的思想。1879年,托马斯主义最终也被天主教教会宣布为正统哲学。1931年,教皇颁布了新的规定,教会大学里的哲学和思辨神学课程必须按照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和原则进行讲授。
与此相联系,托马斯主义在十九和二十世纪经历了一次重要的复兴。在所谓的新经院哲学——这是一个波及整个天主教世界的思想运动,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出自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和德国——的框架内,产生了一种新托马斯主义哲学,这种哲学试图将现代科学和哲学的研究成果与托马斯所创立的天主教宇宙观糅合到一起。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我们还要对托马斯主义的现代发展作简要阐述。
并非光荣的一页
针对几乎所有的中世纪思想家,我们都可以提出指责。由于托马斯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我们在这里也就从他入手了,看一看他的影响有多深。
问题涉及的是,相信有魔鬼和女巫。《神学大全》里有下面一段话:“奥古斯丁写道:许多人声称,他们曾经亲历过或听其他亲历过的人说过,森林之神常常会调戏妇女,渴望与她们同房并且也这样做了。因此,若否认这一点就是厚颜无耻。”在另一个地方,托马斯又说:“逍遥学派认为根本就没有魔鬼,这显然是错误的观点。”
任何时代都有人会相信,的确有魔鬼和女巫。在《旧约》中对此也有过描述(参见撒母耳记上第28章,扫罗让隐多珥的女巫召回死去的撒母耳的亡魂,并请他为抵御菲利士人的进攻出谋划策)。
中世纪时,相信有魔鬼也是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在直到十二世纪的几百年里,教会一直把这种现象看作异教迷信的残余,对它基本上表示容忍或较为温和的抵制。渐渐地开始流传一种说法,说女巫们之所以拥有特异功能(比如她们能在黑夜里腾云驾雾,或者能使人和动物丧失生殖能力)是因为她们与魔鬼撒旦缔结了契约。在当时,相信有魔鬼的人之所以那么多,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受教会抵制的许多教派被视为黑暗的魔鬼世界的代表,它们是与上帝的光明世界相对立的。
谁要是与魔鬼结成同盟,那么他就是反对上帝的,因而他也是反对教会的,因为教会就是上帝在尘世的代表。于是,谴责装神弄鬼的巫术渐渐地就与谴责异端邪说融合到了一起。宗教法庭原来是审判那些偏离宗教信仰的异端分子的,如今它也用来审判巫师了。许多教皇都授权宗教法庭对巫师的审判,1252年,教皇英诺森九世授权宗教法庭可以使用刑罚。
大约在十五至十八世纪,对巫师的迫害才真正达到高潮,教皇英诺森八世于1484年颁布的教谕对迫害巫师的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比那两位多明我教徒和异端裁判官海因里希·尹斯提托利和雅各布·施普朗格发表著名的《打击巫师之锤》(拉丁文为Malleus malificarum,1485年)还早一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本书是除《圣经》之外最畅销的书,成为迫害巫师的专业性手册。
焚烧异教徒和女巫的火焰熊熊燃烧了两个半世纪之久,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被烧死的人加起来共计有十万之多,另有人则认为,牺牲者远远不止这个数目。被烧死的人中,大部分是女人。只要有人告发,就足以开庭审判。在酷刑面前,几乎所有人都会招认最为荒唐的罪行。这种迫害行为基本上都发生在中欧和西欧(西班牙、法国、瑞士、意大利、英国、德国和波兰),而在伊斯兰教、犹太教和东正教地区,却并没有发生这种迫害行为。随着殖民地的开发,这种疯狂的行径也被带到了海外,1692年,大火又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萨勒姆燃烧了起来。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这种迫害行为逐渐停止下来,这主要是弗里德里希·冯·施佩和克里斯蒂安·托马修斯的功绩。德国最后一次焚烧女巫事件发生于1775年。
必须考虑的是,谁要是胆敢相信巫师,那他自己就将会遭到宗教法庭或世俗法庭的迫害。就托马斯来说,我们必须考虑到,他相信魔鬼和巫师的观点几乎为他那个时代的所有神学家和哲学家所熟知,而且也为宗教改革家路德和兹文格利所熟知。由于托马斯的伟大权威性,他的观点当然也会受到特别关注。在《打击巫师之锤》一书中,他的名字就曾经被无数次提到。
-

- 5G时代来临,这些专业“最吃香”,月薪过万!(填志愿注意了)
-
2024-11-11 02:29:59
-

- 民主的虚伪之美国内战
-
2024-11-11 02:27:44
-

- 奇异博士中的古一法师为什么会死去?
-
2024-11-10 12:03:03
-

- 美国科州下起“塑料雨”!研究称九成雨水含塑料纤维
-
2024-11-10 12:00:48
-

- 联发科Helio P90安兔兔跑分曝光:超16万,性能接近骁龙710
-
2024-11-10 11:58:33
-

- 外省人:什么!你们广东人冬至竟然不吃饺子
-
2024-11-10 11:56:19
-

- 军人手机壁纸:每张画面蕴含着军人独有的荣耀
-
2024-11-10 11:54:04
-

- 花体字纹身图案
-
2024-11-10 11:51:49
-
- “从前有座山"故事新编
-
2024-11-10 11:49:34
-

- 日本百合漫画citrus柑橘味香气迎来结局 橘里橘气两女主终成眷属
-
2024-11-10 11:47:19
-
- 情人节
-
2024-11-10 11:45:05
-

- 精选二次元风格星空美景图
-
2024-11-10 11:42:50
-

- 方大曾:消逝在硝烟炮火中的“战地特派员小方”
-
2024-11-09 12:54:43
-

- 大汉奸汪精卫的6个子女结局?一个夭折,另5个全长寿,有钱有势
-
2024-11-09 12:52:28
-

- 超级富豪之路:何猷亨的惊人蜕变!
-
2024-11-09 12:50:13
-
- LPL全明星走红毯后,电竞主播智勋发文,想向天再借5厘米身高
-
2024-11-09 12:47:58
-

- 这种花有特殊的味道,女孩闻着常常害羞,专家称女生闻到不会怀孕
-
2024-11-09 12:45:43
-

- 玉米粒挂钩的正确姿势原来是这样的,多数钓鱼人都做错了!
-
2024-11-09 12:43:28
-

- 星学院:魔法师专属特效,一个比一个华丽,美星其实是蔷薇公主
-
2024-11-09 12:41:14
-

- 我与中年女性的亲密接触:不得不说的几点心得!
-
2024-11-09 12:38:59



 省长工资的简单介绍
省长工资的简单介绍 鄂州地区抢先一步,葛店率先并入武汉,下一个会是哪个城市?
鄂州地区抢先一步,葛店率先并入武汉,下一个会是哪个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