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评-《逃出绝命镇》:遵循中的冲撞
影评-《逃出绝命镇》:遵循中的冲撞
遵循中的冲撞一评电影《逃出绝命镇》
《逃出绝命镇》 (《Get Out》) 于2017年2月在美国上映, 由好莱坞集编、导、演、制片于一身的全能青年导演乔丹·皮尔担任编导。这部影片虽然是乔丹·皮尔由电视剧转战大银幕的电影处女作, 却获得了2018年第90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两项重量级奖项提名。一个38岁的青年黑人导演以一部小成本惊悚片处女作得到了“老成持重”的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首肯, 不得不说是一个绝对的小概率事件, 想必乔丹·皮尔本人也始料未及。
剧情上看, 它是混合了悬疑、科幻、逃杀等多种元素于一体的惊悚片类型。我们知道, 电影类型的作用是在最短的时间内让观众通过长期观影所积累下的经验和形成的思维对所观看的影片产生一种心理预期和渴求。类型是有套路的, 具体到惊悚片这一类型, 大部分都是这样一个路数:最开始展示一个受害的场景, 先营造出气氛, 然后主人公登场, 从最初安全稳定的状态到被引导或在无意间一步步接近危险, 大概在影片中段偏后的部分落入谷底。在此之前还要设置一个或多个自救或他救的情节线, 之后的绝地反击中, 这条线索会发挥重要作用, 使主人公的不利局面得以改变, 进而发生反转, 迎来高潮的对峙后故事结局 (或成或败) , 最后还可能留下一个开放性结局, 暗示罪恶并未被完全清除。
虽然类型片的演进有着如此明晰的套路, 但还是被绝大多数商业电影所采用, 因为套路并非类型片的核心, 对于套路的遵循及冲撞才是类型片的核心。遵循使得观众得到“意料之中”的满足感, 冲撞产生的是不确定性和“原来如此”的恍然大悟感, 这两种感觉缺一不可。失去遵循会让观众感到不知所云的迷茫或脱离轨道的不适, 失去冲撞会让观众觉得平庸、乏味。因此, 好的类型片一定是在这两者的奔突中做到合理的配置, 达到极佳的平衡。具体到《逃出绝命镇》这部电影, 故事的结构、悬念的营造、解决的方式体现出了对惊悚片类型的遵循, 而其体现出的深层思考和对世界的认知, 则大大超越了一般的惊悚片, 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成为2017年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与良好口碑的佳作。
《逃出绝命镇》遵循了惊悚类型电影的套路, 又在每一个环节上用心构思, 可谓遵循套路又不落俗套, 尤其是结束后再回想之前的细节, 设计之精巧、呼应之紧密让人大为赞叹, 这证明类型并非简单重复, 好不好关键在于精不静、巧不巧。
《逃出绝命镇》对于惊悚片类型的冲撞主要体现在它超出一般惊悚片的思想含量及深度, 对社会学乃至哲学问题进行了电影化的思考。
从最表象的层面来看, 它含有对种族主义这一毒瘤和顽疾的表现:片中的黑人成为了白人猎取的对象, 白人赞叹黑人强健的身体, 却对自己的智力和思想更为自负;黑人被认为是危险的人种而被严苛地对待;罗德试图报警, 警官却认为他有病, 没有人相信在当今社会会公然存在这种针对黑人的种族歧视行为, 尽管这三个警察中, 两个是黑人, 一个是拉丁裔。
如果以民族命运与文化独立性的关系来解读这部影片, 又可以轻易地看出文化渗透的隐喻及由之产生的焦虑:白人文化对黑人文化的渗透, 西方文化对发展中国家文化的渗透, 民族文化特性消失的危机, 话语体系的西化倾向, 都可以从影片中“意识对身体的控制”中得到映射。当自己的身体被异质的头脑所控制, 那个所谓的自己便已不是自己, 因为决定自己非彼是此的是思想而不是身体。
甚至还可以进行这样的思考与解读———活体间大脑移植固然是不道德、反伦理甚至反科学的, 但如果是将死者的大脑进行移植那么如何评价?试想如果能够在技术上实现, 那么将爱因斯坦的大脑移植给一位脑死亡的科学家是应该肯定还是反对?如果大脑可以移植, 那么其他器官、肢体是否可以移植?是否进而可以进行人种的选择和优化?而这不正是希特勒倡导并推行的?怪不得影片中父亲迪恩在准备给盲人画廊经营者手术时优雅而准确地切掉头皮, 锯开头骨时的配乐并不是疯狂而恐怖的声响, 反而是庄重、肃穆, 充满崇高意味的男女声合唱, 这一瞬间, 我竟想起了雷芬斯塔尔, 想起了《意志的胜利》, 想起了纳粹, 或许这也是导演选择《run rabbit run》这样一首与“二战”渊源极深的歌曲作为配乐并分别出现在片首和片尾的原因。
此时, 我感到不寒而栗, 不是因为想起了纳粹, 而是想到在全世界的生物和医学实验室里, 多少能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实践正在以造福人类的名义夜以继日地进行。或许, 《逃出绝命镇》使人惊悚的并非它的假设, 而是它所表现的现实。



-

- 也许你知道小天狼星布莱克,但你知道其他阿尼马格斯吗?
-
2025-03-05 01:46:47
-

- “自驾敦煌8000余公里”第一天:宿宣化、吃烤羊腿、莜面窝窝
-
2025-03-05 01:44:3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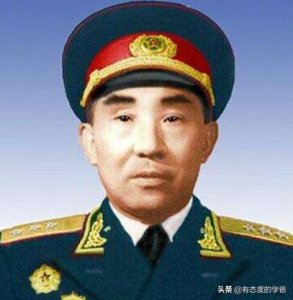
- 中央红军长征时,12个师的师长都是谁?55年分别授予了什么军衔?
-
2025-03-05 01:42:18
-

- 因被抄袭,China Mac线下约架美国电台主持人
-
2025-03-05 01:40:03
-

- 「驾驶技巧」建议所有手动挡驾驶爱好者,都去学跟趾动作
-
2025-03-05 01:37:48
-
- 图说内大-带你看看内蒙古大学南校区|宿舍、食堂到底长啥样
-
2025-03-05 01:35:33
-
- 世界围棋史高手排行榜
-
2025-03-05 01:33:19
-

- 石家庄周围自驾一日游线路:西柏坡,万寿寺塔林,东林山
-
2025-03-05 01:31:04
-

- 演员王晓晨泳装照 身材火辣迷人
-
2025-02-26 20:13:27
-

- 王者荣耀中杨戬埃及法老和永耀之星的台词
-
2025-02-26 20:11:12
-

- 世界上最丑的三种鱼,丑得令人难以想象
-
2025-02-26 20:08:58
-

- 圣巴特岛上游玩,居然能碰上胆大的它
-
2025-02-26 20:06:43
-

- 盘点六位张三丰扮演者,李连杰的太经典,焦恩俊的帅气无人能及
-
2025-02-26 20:04:28
-

- 你的手机号值多少钱?
-
2025-02-26 20:02:13
-

- 怀化市历任市委书记、市长
-
2025-02-26 19:59:58
-

- 黑色人种_尼格罗人
-
2025-02-26 19:57:4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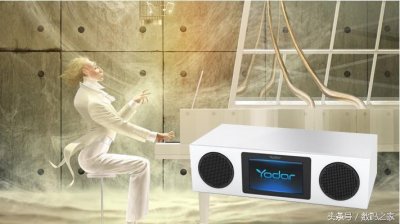
- 高保真?什么是高保真?
-
2025-02-26 19:55:29
-
- 戴戒指五个手指的含义
-
2025-02-26 19:53:14
-

- 李小璐首晒内八字脚照片,称自己是大家闺秀!网评却指众多错误!
-
2025-02-26 14:30:06
-

- 绝地求生知名主播Kots-酒客教你如何用S1897成为巷战之王
-
2025-02-26 14:27:51



 省长工资的简单介绍
省长工资的简单介绍 鄂州地区抢先一步,葛店率先并入武汉,下一个会是哪个城市?
鄂州地区抢先一步,葛店率先并入武汉,下一个会是哪个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