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耳的自我坚守,注定让《无名》与众不同
程耳的自我坚守,注定让《无名》与众不同
这个春节档,程耳导演的《无名》恐怕是最命运多舛的一部电影。基于对主创阵容的万众期待以及对程耳作品质量的信心,预售期票房可谓遥遥领先。但随着电影正式面向大众,影片的口碑却毁誉参半,导致票房后劲不足。

纵观网络上的差评,不喜欢的观众各有各的理由,针对故事、表演、剪辑等提出诸多异议;而喜欢这部电影的观众,则对程耳的执导功力赞不绝口,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评价是:这部电影尊重了我的审美和智商。

面对这样的争议,程耳导演也在网上坦诚发声:“电影拍完,导演不应该过多地去讲解,我的作用已经发挥完了,我想表达的,都在电影里了,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你们的反馈,好奇,困惑,兴奋,满意,对电影来说,是这些声音成全了它更有意义。”这段话让我笃信,即便已然时过境迁,但程耳依然还是那个用心拍电影的好导演,正如前辈侯孝贤曾经说过的“背对观众”。

这些年来,观众们对于春节档似乎早已形成一个思维定式,似乎过年过节就应该看喜剧片,才最符合辞旧迎新的氛围。但说实话,电影市场还是亟需跳出这样的窠臼,亟需容纳更多元化的电影进场,才能更健康、更良性地长久发展。
然而前路漫漫,我们终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或许,有一句话说得很对,电影《无名》并非真的不适合春节档,而是它的成败还需要更长时间的等待,我们才能等到一个真正客观理性的评价。

影片的宣传海报上有句话:隧道尽头终有光。这句话,既是对影片中那些舍身赴死的无名英雄们的深切告慰,即便身陷时代囹圄,我们依然心存希望。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像《无名》这样“需要时间来证明”的电影的勉励,就算眼前的隧道再长,也终会有走到尽头、看见光的那一天。

影片《无名》的时间跨度,是从1937年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期间经历了淞沪会战、广州沦陷、偷袭珍珠港、汪精卫死亡等历史事件。曾经的八年抗战,即便你不曾学过历史,也应该不会陌生。

影片采用非线性叙事,将整个故事的焦点放在孤岛时期(1937-1941)以及孤岛沦陷后(1941-1945)的上海,讲述身处隐蔽战线的地下工作者如何与各方势力殊死较量的过程。程耳导演采用非线性叙事,让故事的整体发展与每个重要历史节点遥相呼应。

这种多线索交叉叙事、多维度谋篇布局的笔法,显然比常见的平铺直叙更有观影快感。有人由此诟病“观影门槛太高”,实在是枉费程耳导演的苦心。但凡你能多专注一点投入到电影当中,就很难不为导演的精心编排拍手称快。

相比春节档的其他几部电影,电影《无名》显然是与众不同的。倘若你曾被程耳导演的前作《罗曼蒂克消亡史》所触动,那一定也会对《无名》心有戚戚。强烈的影像风格,神秘的作者腔调,赋予整部影片独一无二的高级质感。甚至有人赞叹说,程耳导演真正提升了国产谍战片的天花板。

在我看来,他能够以如此沉得住气的个性化创作方式,捍卫自己的影像风格和艺术美学,着实令人敬服。与此同时,动作、悬疑等多重类型元素的融入,则突破前作《罗曼蒂克消亡史》的局限性,在艺术与商业之间达成完美的平衡。
这并非程耳对商业市场的妥协,而是他在主旋律电影的基础上,依然跟随自己的创作理念,坚持保有作者型导演的底色。

最后再来说说演员。影片中,无论主角还是配角,都各得其所,既整体圆融又独具个性。重回民国风的梁朝伟和周迅仿佛就是从“那个年代走出来的人”,贡献出影帝影后级的表演。黄磊、王传君、江疏影、森博之、张婧仪等,也都将他们各自的角色拿捏得恰到好处。


而王一博饰演的叶先生,也的确没有让我们失望。动作戏自不必说,跟梁朝伟的对手戏也没有露怯;还有几场很难演的内心戏,都能自然而然地投射出错综复杂的情感,实属难得。对年轻演员而言,碰上好导演真的是一次演技的磨炼。

程耳导演说,《无名》其实很难用“谍战”、“悬疑”这样简单的标签概括,这部电影是“关于无名者的史诗,是那个年代的挽歌”。在曾经那个暗流涌动、波云诡谲的巨变年代,正是这样一批无名英雄,为我们创造了长久的和平。面对这段被隐去的历史,程耳让我们看到了“无名”背后的意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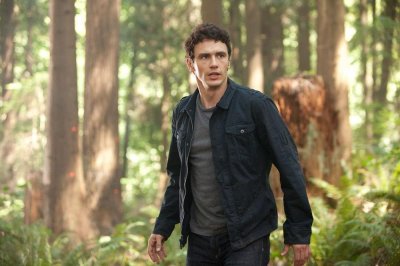
- 安迪·瑟金斯扮演的凯撒已经落幕,为了人族的纯粹选择自杀
-
2025-03-17 19:45:01
-

- 她才是萧穗子原型,被渣男抛弃,惨遭刘峰命运,曾绝望的想自杀!
-
2025-03-17 19:42:46
-

- 十一旅游景点之-恩龙世界木屋村
-
2025-03-17 19:40:31
-

- 孟菲斯美女号、艾森豪威尔都是替代品?一架轰炸机撞山改变了历史
-
2025-03-17 19:38:16
-

- 《亮剑》中选择为尊严而饮弹自杀的赵刚,他的原型到底是谁?
-
2025-03-17 19:36:01
-
- 四个著名的法律小故事
-
2025-03-16 08:52:09
-

- 忠诚许国,老而弥笃 抗倭名将俞大猷
-
2025-03-16 08:49:55
-

- 关于柬埔寨,这些冷知识你都知道几个?
-
2025-03-16 08:47:40
-

- 北京7个充满故事的桥把你走过几座
-
2025-03-16 08:45:25
-

- 「媒体看肥西」《晚间播报》:肥西有群挖藕人,烈日下在淤泥中“淘金”
-
2025-03-16 08:43:10
-

- 《乘风破浪》首播刷屏,豆瓣评分为什么却只有6.8分?
-
2025-03-16 08:40:56
-

- 丧事随礼,多少合适,有什么讲究
-
2025-03-16 08:38:41
-

- 成都坐火车到西宁兰州乌鲁木齐 周四起将节省8-10小时|早读四川
-
2025-03-16 08:36:2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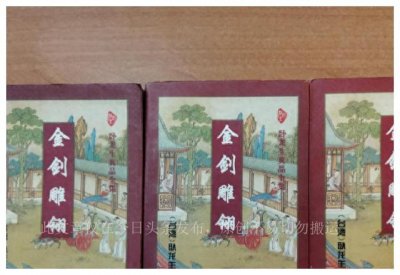
- 武侠小说10大神作,武侠迷必看,每一本都是经典
-
2025-03-16 08:34:1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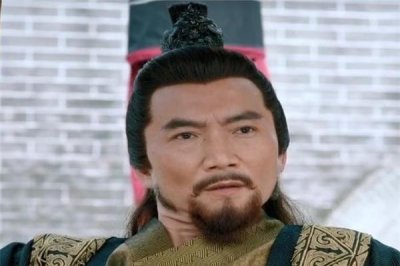
- 狐族冒充仙人参加九龙宴,惨遭祸害,妲己为何此时才启用胡喜媚?
-
2025-03-16 08:31:5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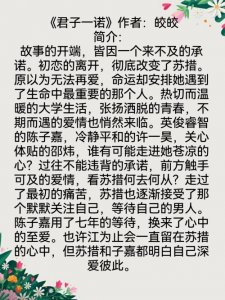
- 皎皎的8部经典小说:如果最后来的人是你,我等得久一点也没关系
-
2025-03-15 11:54:34
-

- 东北营口坠龙事件,发现一具庞大的怪物尸骸
-
2025-03-15 11:52:19
-

- 中国十大名酒品牌排行榜!你知道几个?
-
2025-03-15 11:50:0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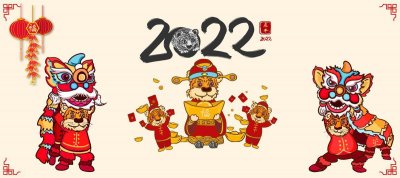
- 北京跨年来这里!这6个地方必收藏,你准备好去哪里跨年了吗?
-
2025-03-15 11:47:49
-

- 阳池穴-调理“手足冰凉、落枕、肩周炎”的原穴
-
2025-03-15 11:45:35



 省长工资的简单介绍
省长工资的简单介绍 鄂州地区抢先一步,葛店率先并入武汉,下一个会是哪个城市?
鄂州地区抢先一步,葛店率先并入武汉,下一个会是哪个城市?